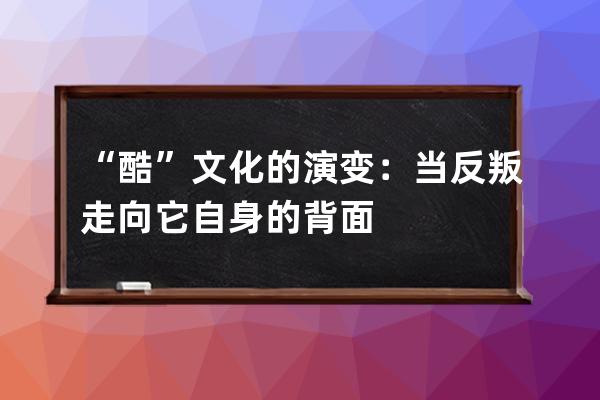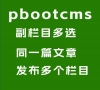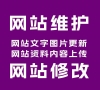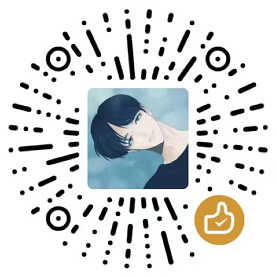“酷”文化的演變:當(dāng)反叛走向它自身的背面
近日,加拿大學(xué)者喬爾·迪內(nèi)斯坦(Joel Dinerstein)出版了新書(shū)《酷的起源》。在這本有趣的書(shū)中,他詳細(xì)梳理了“酷”的脈絡(luò)。正如書(shū)中所指出的,“酷”文化本身與現(xiàn)代西方社會(huì)、政治、文化的變遷密切相關(guān)。很大程度上起著邊緣或者非主流力量的作用。
然而,目前存在于許多文化界的“酷”文化大多停留在對(duì)消費(fèi)主義的有限理解上。在韓國(guó)練習(xí)生公司受訓(xùn)的明星,可能對(duì)如何擺“酷”了如指掌;然而,在被認(rèn)為懂得“酷”的說(shuō)唱圈里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了咄咄逼人的陽(yáng)剛之氣的蔓延,以及他們對(duì)“酷”文化的象征性利用。在抖音、Aauto Quicker或小紅的書(shū)等各種“酷小伙、酷姑娘”中,不如說(shuō)在這些極具商業(yè)利益的流行平臺(tái)中,“酷”文化早已走到了它的背后,成為機(jī)械復(fù)制時(shí)代大規(guī)模生產(chǎn)的文化模式。而我們對(duì)它的理解,總是隔著一個(gè)屏幕,陷入它對(duì)贊美的需求。
目前,光怪陸離的社交媒體上充斥著這樣的沖突。一種流行文化,在曾經(jīng)的反叛背道而馳的情況下,我們應(yīng)該如何看待它的興起、挪用和再創(chuàng)造?
“酷”的當(dāng)代形象
西方現(xiàn)代的“酷”文化終于隨著全球化和西方發(fā)達(dá)的文化產(chǎn)業(yè)迅速傳播到其他文化中,并因其迷人的特質(zhì)而經(jīng)常受到許多年輕群體的歡迎。“酷”和年輕人的親密關(guān)系,大多是由他們?cè)谥髁魃鐣?huì)文化和結(jié)構(gòu)中的地位決定的。正統(tǒng)文化本身就包含著強(qiáng)烈的父權(quán)形象,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隱藏在“酷”文化中的非常鮮明的“弒父”情結(jié)。
在1955年的電影《無(wú)緣無(wú)故的叛亂》中,詹姆斯·迪恩飾演的吉姆憂郁、敏感,總是被排斥。吉姆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一種典型的形象,即疏離家庭和社會(huì),并表明了這些年輕人對(duì)他們過(guò)于嚴(yán)肅、正統(tǒng)和霸道的“父親”的不滿。迪內(nèi)斯坦、詹姆斯·迪恩、馬龍·白蘭度、貓王創(chuàng)造的文化形象被稱為“美國(guó)叛逆酷”。
詹姆斯·迪恩(左)在《無(wú)緣無(wú)故的叛亂》(1955)中扮演吉姆。
《教父》(1972)中的馬龍·白蘭度。
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(guó),年輕人的酷首先意味著反叛,是對(duì)傳統(tǒng)父輩所構(gòu)建的制度和文化體系的一種對(duì)抗,希望塑造一個(gè)屬于自己的新的人格和形象。這種對(duì)新人格的追求在隨后的“嬉皮士一代”中達(dá)到了頂峰,也成為了隨后的“酷”文化中的核心氣質(zhì)。在1961年的《巴黎之戀》中,逃離塞納河的美國(guó)青年想象他們?cè)趧e處(蘭博)的生活,有趣的是,法國(guó)存在主義哲學(xué)本身就包含了構(gòu)建后來(lái)“酷”文化的重要元素。
《巴黎瘋狂》劇照(1961)。
在加繆的存在主義中,西西弗斯是他最經(jīng)典的形象:個(gè)體對(duì)存在處境的荒謬意識(shí),以及由此引發(fā)的無(wú)限而似乎注定的悲劇性反抗。相比于60年代美國(guó)年輕人的淡然反叛,經(jīng)歷過(guò)二戰(zhàn)、在反抗運(yùn)動(dòng)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加繆,依然顯得更沉重、更憂郁,就像他留給后人的黑白影像中所展現(xiàn)的形象:眉頭深鎖,表情嚴(yán)肅。即便如此,在某種程度上,他們還是能找到彼此的核心,那就是對(duì)個(gè)體自由和個(gè)性的向往和追求。
加繆
20世紀(jì)50、60年代由西方年輕人構(gòu)建的“酷”文化,此后隨著新的社會(huì)文化形勢(shì)發(fā)生了變化,但其核心始終是它能被年輕人,尤其是不在西方的年輕人歡迎和接受的主要原因。而且這些文化在特殊時(shí)刻出現(xiàn),很快就會(huì)成為年輕人愛(ài)上的思想資源和生活方式。比如上個(gè)世紀(jì)改革開(kāi)放之初,年輕人通過(guò)模仿西方的服飾、發(fā)型、愛(ài)好,表現(xiàn)出一種不同于父輩的生活和人格的新的可能性,使得當(dāng)時(shí)的藝術(shù)、搖滾樂(lè)、文學(xué)都有了新的面貌。
跨文化流動(dòng)的“酷”文化
2002年,一個(gè)輟學(xué)的女孩春樹(shù)出版了一部小說(shuō),名叫《北京娃娃》,副標(biāo)題是《一個(gè)十七歲少女殘酷的青春自白》。小說(shuō)的封面上,短發(fā)的女孩盤著腿,以冷漠對(duì)抗的姿態(tài)看著讀者;整個(gè)照片風(fēng)格,Pop,很符合它希望傳達(dá)的氣質(zhì)。在封面邊緣,這本書(shū)的英文名是“I,Seventeen,bad Girl”……整部小說(shuō)從設(shè)計(jì)、裝幀到內(nèi)容都透露出一股強(qiáng)烈的顛覆氣質(zhì),或許是為了呼應(yīng)媒體上“春樹(shù)”這個(gè)叛逆壞女孩的形象,讓很多人把這部小說(shuō)當(dāng)成了作者的自傳。
《北京娃娃》,作者:春樹(shù),版本:磨鐵叢書(shū)|遠(yuǎn)方出版社,2002年5月
春樹(shù)可以說(shuō)是21世紀(jì)初中國(guó)最具代表性的“壞女孩”形象。在她的小說(shuō)里,女孩輟學(xué),叛逆,在性和愛(ài)情上奔放。她的形象顛覆了傳統(tǒng)對(duì)女生的要求,在充滿禁錮和規(guī)范的學(xué)校里胡作非為。春樹(shù)在媒體上的形象也是前衛(wèi)時(shí)尚的。她在2013年出版的詩(shī)集《春樹(shù)的詩(shī)》封面上,一個(gè)留著粉色短發(fā)、戴著墨鏡、穿著黑色皮衣的女人形象,依然延續(xù)著她出現(xiàn)在美國(guó)《時(shí)代》雜志上的朋克氣質(zhì)。或許是為了追求當(dāng)時(shí)在中國(guó)流行的日本“殘酷青春”電影和文學(xué),所以春樹(shù)在媒體和她的小說(shuō)中的形象都偏向于“壞女孩”,但或許更準(zhǔn)確的說(shuō)法應(yīng)該是“酷女孩”。春樹(shù)的作品和形象所揭示的,與其說(shuō)是日本青年的殘酷——它往往攜帶著更多陰郁內(nèi)斂的東方氣質(zhì)——不如說(shuō)是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更多地來(lái)自西方的朋克、搖滾和酷文化。她的憤怒是公開(kāi)的,明目張膽的,有針對(duì)性的,暗示著在這個(gè)老齡化的社會(huì)氛圍中,一種新的勇敢力量的爆發(fā)。
春樹(shù)的形象很少被傳承,或者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圈子和群體中。但背后的主要原因是,隨著社會(huì)的變遷,尤其是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的發(fā)展和消費(fèi)文化的興起,酷文化或曾經(jīng)桀驁不馴的文化形式逐漸被商業(yè)化或被推到邊緣(如搖滾樂(lè))。曾經(jīng)全國(guó)聞名的“壞男孩”韓寒,如今也開(kāi)始在電影中反復(fù)消費(fèi)自己早年構(gòu)建和積累的形象。寫三重門時(shí)期的韓寒真的很酷。他留著長(zhǎng)發(fā),瀟灑的輟學(xué),經(jīng)常像《國(guó)王的新衣》里的男孩一樣戳中許多陳腔濫調(diào)。但是,這樣的“冷靜”本身似乎最終也沒(méi)能成為他生活和思想的風(fēng)格,或者說(shuō)是伴隨著新的形勢(shì)發(fā)生了新的變化。
這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“酷”文化作為一種跨文化流動(dòng)在異國(guó)他鄉(xiāng)的轉(zhuǎn)化,即相對(duì)于它在西方已經(jīng)成為一種生活或個(gè)體的存在主義哲學(xué)和風(fēng)格而言,我們對(duì)它的理解或接受似乎總是處于一種工具化或極度時(shí)間敏感的狀態(tài)。
似乎只是結(jié)合青春叛逆期而生的成長(zhǎng)狀態(tài)。一旦它過(guò)了這個(gè)階段或者“長(zhǎng)大”,這樣的“酷”就會(huì)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回歸父系血統(tǒng),完美地完成這種形象和存在的轉(zhuǎn)換。與酷年輕人的親密關(guān)系在這里是固定的,“酷文化”似乎是特定年輕人專屬的文化,而成熟人的“酷”往往被認(rèn)為是對(duì)老年人的不尊重或過(guò)分輕浮。
“酷”已經(jīng)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。
“酷”被理解為一種表演,一種面具,一種應(yīng)付家庭、學(xué)校或社會(huì)管教的臨時(shí)調(diào)解或?qū)构ぞ摺;蛟S這恰恰與我們對(duì)“酷”的理解有關(guān)。但正如迪內(nèi)斯坦在《酷的起源》中指出的,“酷”本身是一種開(kāi)放的、完整的哲學(xué),是一種存在狀態(tài),是一種生活方式;而“酷男”本身就是個(gè)體存在的一種形式,而不是某種遮蔽個(gè)體的面紗。只有通過(guò)這種理解,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“嬉皮士”,什么是“酷人”。
《酷的起源》,[加]喬爾·迪內(nèi)斯坦著,汪聰譯,版本:浙江大學(xué)出版社,2022年3月。
正是對(duì)“酷”的有限理解,加上消費(fèi)主義對(duì)傳統(tǒng)邊緣理念或風(fēng)格的吸收和再創(chuàng)造營(yíng)銷,使得“酷”在21世紀(jì)第一個(gè)十年后發(fā)生了新的變化。“酷”已經(jīng)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,尤其是在西方好萊塢電影、超級(jí)英雄文化和明星形象中。隨著“一切固體的東西”被輕量化,在消費(fèi)大潮中變得無(wú)處不在、大行其道,“酷”文化的憂郁及其社會(huì)壓抑的癥狀也開(kāi)始被一種更加積極、輕盈、淡然的氣質(zhì)所取代。
“要酷”的意思是“嘿,不要太認(rèn)真,不要太嚴(yán)肅”,“不要把生活看得太嚴(yán)重”,“為什么這么嚴(yán)重”……與社會(huì)抑郁癥的憂郁癥狀不同,當(dāng)代的“酷文化”改變了對(duì)社會(huì)抑郁癥的看法,從而調(diào)整了其治療和應(yīng)對(duì)方式。
《無(wú)緣無(wú)故的叛亂劇照》(1955)。
所以,面對(duì)那些沉重的、壓迫性的、制度性的問(wèn)題,年輕人開(kāi)始選擇一種更曲折的方式來(lái)處理由此引發(fā)的問(wèn)題。他們不再選擇感到沮喪或痛苦,因?yàn)樗麄円庾R(shí)到壓抑和紀(jì)律的力量,以及他們對(duì)此無(wú)能為力。而是選擇更輕松有趣的方式和他們打游擊戰(zhàn)。只有這樣,我們才能避免前者對(duì)孤立個(gè)體的絕對(duì)傷害,同時(shí)選擇保護(hù)自己以更輕的方式解決這些緊迫的問(wèn)題:樂(lè)在其中!
《黑暗騎士》劇照(2008)。
這些看似消極的“酷”行為和新的生活方式本身其實(shí)蘊(yùn)含著巨大的對(duì)抗性。我們可以從諾蘭的《黑暗騎士》中小丑的形象看出這種新的“酷”文化的潛在力量。小丑的人生哲學(xué)是“何必那么認(rèn)真”?他以憤世嫉俗的態(tài)度面對(duì)傳統(tǒng)的善惡和道德秩序,以他尼采式的虛無(wú)主義,打擊我們作為文明基石的各種觀念,指出它們的虛偽和脆弱。
“酷”的再創(chuàng)造
相比更傳統(tǒng)、更典型的超級(jí)英雄蝙蝠俠,小丑更“酷”。他將其中的憂郁、對(duì)抗、輕盈推向極致,造成了必然的虛無(wú):一切都可以“快樂(lè)”,最終必然走向無(wú)聲的黑暗。這正是存在主義的冷靜所抵制和反對(duì)的。桀驁不馴的“酷”本身就是創(chuàng)造一種新的個(gè)體存在和生活方式的手段,而不是消滅和摧毀其必然需要的個(gè)體和群體生活。
小丑是“酷”的極致,他真正展現(xiàn)了中國(guó)人“酷”字的含義,就是泛濫,走向極端,導(dǎo)致殘酷和暴虐。我們這里所強(qiáng)調(diào)的當(dāng)代“酷”的“輕”,永遠(yuǎn)是為了展現(xiàn)年輕人面對(duì)問(wèn)題的另一種方式,與他們所敬仰的前輩相比。皮劃艇《在路上》中無(wú)拘無(wú)束、痛苦不堪的年輕人,終于找到了“父親形象”的壓迫,從而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而那些“酷人”——尤其是“酷哥”——往往不是那些喜歡在各種說(shuō)唱圈子里炫耀自己咄咄逼人的陽(yáng)剛之氣的年輕人。她們大多在壓抑和痛苦中表現(xiàn)出女性氣質(zhì)。
在路上,作者:杰克·凱魯亞克,譯者:陳杰,版本:大魚(yú)圖書(shū)館|湖南文藝出版社,2020年1月
也正是這一點(diǎn)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“酷”本身就是對(duì)傳統(tǒng)的霸權(quán)男性氣概的反抗,它壓抑了男性在充滿情緒和心理創(chuàng)傷時(shí)表現(xiàn)和訴說(shuō)的權(quán)利,導(dǎo)致他們最終成為冷漠沉默的“父親形象”。有趣的是,馬龍·白蘭度和貓王都沒(méi)有在銀幕上扮演過(guò)有父親的角色,而詹姆斯·迪恩在他的三部電影中都在與一個(gè)極其暴虐和自律的父親斗爭(zhēng),無(wú)論這個(gè)父親形象是真實(shí)的還是想象的。
然而,當(dāng)前許多文化界存在的“酷”文化大多停留在消費(fèi)主義和人們對(duì)它的有限認(rèn)識(shí)上。那些在韓國(guó)練習(xí)生公司培養(yǎng)出來(lái)的明星,可能對(duì)如何擺出“酷”的姿勢(shì)了如指掌,對(duì)這個(gè)形象了如指掌,但在他們高度表演的姿勢(shì)下,往往缺乏持久的核心支撐;然而,在被認(rèn)為懂得“酷”的說(shuō)唱圈里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了咄咄逼人的陽(yáng)剛之氣的蔓延,以及他們對(duì)“酷”文化的象征性利用。除此之外,《抖音》、《汽車快車》、《小紅書(shū)》等各種書(shū)籍中的“酷男酷女”,與其說(shuō)是展示自己的個(gè)性和氣質(zhì),不如說(shuō)“酷”文化早已在這些極具商業(yè)利益的流行平臺(tái)中深入人心,成為機(jī)械復(fù)制時(shí)代大規(guī)模生產(chǎn)的文化模式。而我們對(duì)它的理解,總是隔著一個(gè)屏幕,陷入它對(duì)贊美的需求。
“保持冷靜& ampHave Fun”(耍酷&玩得開(kāi)心)可能是當(dāng)代“酷”文化的口號(hào),但我們不能只根據(jù)字面意思來(lái)理解這句簡(jiǎn)單的話。與其說(shuō)是口號(hào),不如說(shuō)是一種個(gè)體的生存哲學(xué),一種生活方式,一種新的社會(huì)關(guān)系和世界的理念。
在迪內(nèi)斯坦梳理的二戰(zhàn)后西方“酷”的文化變遷中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從爵士樂(lè)、黑色電影開(kāi)始,“酷”的形式總是與時(shí)俱進(jìn),但即便如此,它也總是象征著某種疏離、異化的存在。然而,也許正是那些被邊緣化、被排斥的群體建構(gòu)了“酷”的形象和文化歷史,而這些人本身就象征著他們所處的社會(huì)和政治環(huán)境的癥狀。
小丑劇照(2019)。
在托德·菲利普斯2019年的電影《小丑》(The Joker)中,“小丑”不是某種外來(lái)的災(zāi)難,而是高譚市制度本身的象征性形象。“酷”作為邊緣群體創(chuàng)造的一種新的個(gè)體存在和生活方式,最終獲得了自己獨(dú)立自主的地位,從而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力量,能夠在隨后的全球文化交流中展現(xiàn)出其瑰麗迷人的影響力。
作者|崇木
編輯|行走
校對(duì)|趙琳
如果您的問(wèn)題還未解決可以聯(lián)系站長(zhǎng)付費(fèi)協(xié)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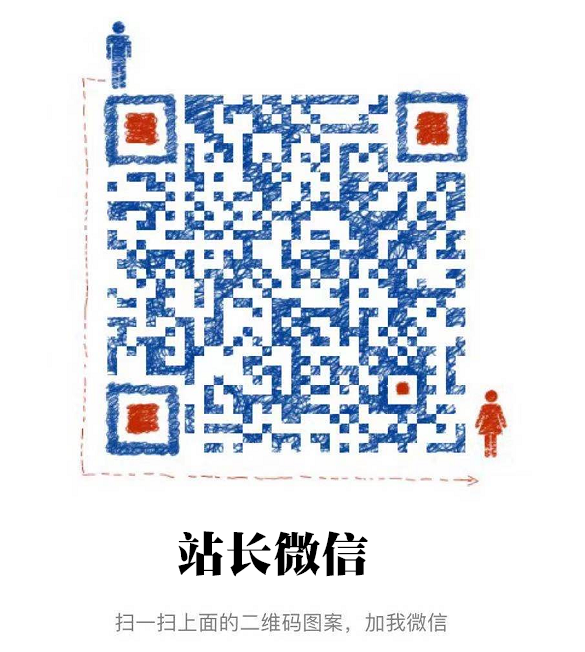
有問(wèn)題可以加入技術(shù)QQ群一起交流學(xué)習(xí)
本站vip會(huì)員 請(qǐng)加入無(wú)憂模板網(wǎng) VIP群(50604020) PS:加入時(shí)備注用戶名或昵稱
普通注冊(cè)會(huì)員或訪客 請(qǐng)加入無(wú)憂模板網(wǎng) 技術(shù)交流群(50604130)
客服微信號(hào):15898888535
聲明: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(nèi)容,如無(wú)特殊說(shuō)明或標(biāo)注,均為采集網(wǎng)絡(luò)資源。如若內(nèi)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(quán)益,可聯(lián)系站長(zhǎng)刪除。